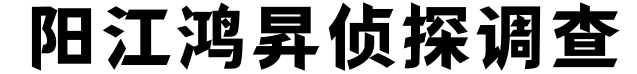“陈阳,鱼汤要凉了。”
徐薇的说话声从灶间飘来,十分微弱,仿佛一根细小的绒毛掉进了水洼里,几乎没看见水花。
我点了点头,视线依旧落在电脑上显示的建造蓝图上。那是一座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我投入了将近一年的精力,图纸上每一条轮廓都仿佛是我心血的结晶。
汤碗搁在桌上的声音很清脆。
我抬头看去,徐薇已经取下了围裙,面对着我,手里拿着一本书,不过她的目光却投向了窗外。
我们彼此之间,横亘着一张不太宽的餐桌,其上放了两样菜与一锅汤,热气升腾,让她容颜变得朦胧不清。
已经结婚五年,按照旁人的看法,我们过着堪称典范的中等收入家庭日子。我在一家声誉良好的建筑设计公司担任负责人,她则在一所舞蹈学校担任首席讲师。家里有一套面积适中的住宅,还有一辆日常使用的汽车,目前没有孩子,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矛盾。
一切都像我画的设计图一样,精准,稳定,找不出一丝差错。
我内心总感觉,名为婚姻的殿堂,其内部结构出现了不易察觉的损伤。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或许是她开始频繁地“加班”,舞蹈课需要排练到深夜。
可能是她身上飘来一种我从未闻过的香味,是清雅的木香,与我赠予她的花果气息大相径庭。
又或许,是她接电话时,总会有意无意地走到阳台去。
我问过一次。
她那时正贴着一张面膜,说话时声音不太清楚,说新来的工作人员,体味比较浓,是无意中弄脏的。
这个说明,好比一块形状不合适的砖头,勉强嵌进了墙中,显得十分突兀。整体非常不匹配,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但我没有再问。
当前我的工作处于一个重要阶段,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应对那些无端的揣测。我明确地意识到,稳固的感情是婚姻的根本。一旦这个基础发生动摇,整个关系就会崩溃。
我宁愿相信,是我想多了。
我关掉电脑,端起汤碗,喝了一口。鱼汤很鲜,火候正好。
“好喝。”我说。
她仿佛猛地清醒过来,朝我露出一个微笑,那个笑容十分常规,嘴角上扬的形态,如同用圆规精确勾勒而成。
“慢点喝,别烫着。”
她的视线在我的脸庞上逗留了不足两秒,随即又转向那本平展的书籍。书卷已经许久未曾翻动页码了。
那个晚上,我平躺床上,明确听见她隐忍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声。
那声音,像白蚁啃噬木头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那天我提早离开了工作岗位,打算给她一个意想不到的问候。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了。
我特意绕路去买了她最喜欢的那家店的栗子蛋糕。
车子驶入院落,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自家的玻璃门。里面透出光,感觉挺温馨。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卡宴在我们楼下停稳。
那车,和我们这个普通小区显得有些不搭。
车门打开,徐薇从副驾驶上走了下来。
她身上披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服饰,并非她惯常钟爱的棉质麻布款型,而是一件轮廓分明的真丝长袍,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颇有几分差异。
司机也下来了。他身材高大,身穿合身西装,腕上的手表在路灯下闪闪发亮。
我认识林峰这个人,他是在校友聚会时多次碰到的对象,家里从事房地产行业,可以称作是颇具才干的新时代商人。
林峰绕过来,很自然地帮徐薇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
徐薇没有躲。
然后,他伸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腕,低声说了句什么。
徐薇微微颔首,面容展现出我从未观察到的复杂情绪。那既非欢欣鼓舞,也并非抵触情绪,而似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认同。
我坐在车里,手里的栗子蛋糕盒子被我捏得变了形。
车窗的玻璃冷得像冰块,阻隔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外面是她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里面是我面对着整个正在瓦解的判断。
我没有下车。
我看着林峰开车离去,看着徐薇走进单元门。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关闭了引擎,提着那个破损严重的蛋糕包装盒,往楼上走去。
我推开门时,她正站在玄关换鞋。
她重新穿上了日常的棉质长裙,望见我时,神情掠过一抹难以察觉的惊惶。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项目提前弄完了。”我把蛋糕放在鞋柜上,声音很平。
我能闻到她身上残留的,那股淡淡的木质香。
她看到了那个变形的盒子,眼神闪烁了一下,“这是什么?”
“蛋糕。”
我换好鞋,没有看她,径直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
她跟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小心翼翼地,像怕惊扰到什么。
“陈阳,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她。
她的手,就是刚才被林峰握过的那只手,正不安地绞着衣角。
沉默像浓雾一样,充满了整个客厅。
最后,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陈阳,我需要你相信我。”
“我看见你从林峰的车上下来了。”我终于说了出来,声音比预想的更加干涩。
“是。”她没有否认,这让我心里那点仅存的侥G幸也熄灭了。
“他碰了你。”
“是。”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呼吸都变得困难。
“所以,是真的。”我说。这不是一个问句。
她只是轻轻摆了摆头,目光紧紧锁定在我身上,里面藏着我无法理解的期盼和倦意。
“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一场戏,一场……我必须演下去的戏。”
“戏剧?”我差点失笑。这个词,由我朝夕相伴的妻子道出,显得极不现实。
是的,一部戏而已。她再次说道,我家里有个挺棘手的……状况,非林峰不可。他开出的条件是,我必须配合他,假扮成一对情侣,持续一段时间。
她目光直视我,逐字逐句地讲:“我需要你,陈阳情感挽回,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装作感情出现了裂痕,装作你对这件事毫不知情。等麻烦处理完毕,所有都会和从前一样。”
她没有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演戏。
她只是把一个结果,一个需要我接受的剧本,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她,试图从她脸上找到一丝撒谎的痕迹。
但没有。只有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近乎绝望的镇定。
我的思绪非常混乱。设计师的条理清晰头脑忽然无法正常运作了。我无法判断这件事的合理性,也无法构建出一个可靠的说明。
我只知道,我有两个选择。
倒掉器皿,把所有事务都公开,接着或许要承受一次无法补救的瓦解。
二是,相信她。或者说,选择暂时相信她。
我选择了后者。
我无法设想缺少她的日子,那种空虚感,比眼前的怪诞更加难以忍受。
“好。”我说出了那个字。
我注意到她的双肩突然变得不再僵硬,仿佛卸掉了无比沉重的负担。她的眼眶泛红,想要伸出手来拥抱我,但动作却在空中停顿住了。
“谢谢你,陈阳。”
那个晚上,我们分房睡了。
这是我们结婚五年来第一次。
我躺在客房的床上,天花板上的灯光很刺眼。
我同意了配合她演戏。
但我没想到,这场戏的第一个观众,就是我自己。
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舞台。
她不再邀请我共进餐食阳江哪里有可靠的侦探社,而是独自准备食物,装进保温容器中,又在桌上留下纸条。
她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回来,身上会带着淡淡的酒气。
她不再把舞蹈班里的新鲜事告诉我,我也不再把图书馆项目中的困惑对她倾诉。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室友,遵守着互不打扰的默契。
有一次,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和甲方讨论方案。
隔着玻璃窗,我看到她和林峰并肩走过。
林峰手上拿着多个购物袋,袋子上印着高端品牌的标识。徐薇跟在他旁边,略微抬起脸庞与他交谈。阳光照耀下,她脸上绽放的笑容,明媚得让人难以直视。
那一刻,她看起来真的像一个被宠爱的女人。
而我,像一个躲在暗处的、可笑的观众。
甲方在说什么,我完全没听见,只是盯着他们,直到他们不见踪影,拐进了街角。
我开始失眠。
连续多晚都凝视着天花板,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她与林峰相处的情景。
我告诉自己,这是演戏。
人的内心并非坚硬如铁。持续的打击,致使称作“信赖”的缺口,不断加宽。
我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一次审图会上,我把图书馆的消防通道设计出了一个低级错误。
被领导当众点了出来。
我伫立在会场之中,目光与众多视线交汇,脸颊顿时滚烫无比。这经历,是我工作生涯中,头一遭遭遇的难堪场面。
回到家,房子里冷冷清清。
桌上照例放着保温饭盒。
我打开它,里面的饭菜还温着。
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我坐在餐桌前,从天亮坐到天黑。
徐薇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
她看到我坐在黑暗里,吓了一跳。
“怎么不开灯?”
她打开灯,光线让我有些不适应地眯起了眼。
她走近了,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木质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
“你喝酒了?”我问。
“嗯,一个应酬。”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看着她,她的脸颊因为酒精泛着红晕,眼睛里有种迷离的光。
“表演,进行得愉快吗?”我的话语中,夹杂着本人未曾意识到的寒意。
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
“陈阳,你答应过我的。”
我同意你的要求,但我并非愿意盲目忍受,眼睁睁看着伴侣与第三方有亲密行为。
我的情绪有些失控,声音也大了起来。
“你希望我怎样?”她也提高了音量,眼中流露出的疲惫和委屈仿佛即将满溢,“难道我真的乐意吗?难道我每天强颜欢笑,周旋于那些人之间,内心就能安然无恙吗?”
“你能不能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站起身来,向她靠近,“究竟是什么,让你愿意这样糟蹋自己,也毁掉我们之间的情分,却始终不肯透露?”
她被我逼得退后一步,靠在了墙上。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摇着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别问了,陈阳。求你,别问了。”
她的眼泪,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所有的火气。
剩下的,只有无力的冰冷。
我退后几步,重新坐回椅子上。
“我累了。”我说。
“对不起。”她低声说。
那天晚上,我们之间的沉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下去了。
等待,只会让那道裂缝,变成无法逾越的深渊。
我不再是被动承受痛苦的观众了。
我必须知道真相。
不是为了质问,也不是为了报复。
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段关系,寻一个能够立足的根基,不论那根基是否稳固,抑或正面临崩塌的危机。
我开始主动去寻找答案。
我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维持这个看似完整的家,还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答案是后者。
我无法再沉浸在这种虚假和神秘之中。我的心灵,我的事业,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正被这团迷雾所消耗。
我没有选择去跟踪徐薇,那感觉像是在监视一个犯人。
我从另一个方向入手。
林峰。
我借助校友平台,查到了他的部分资料。他的工作单位,还有他的部分商业合作者。
我开始留意一些财经新闻,关注和他公司相关的项目。
我天生对信息与逻辑特别敏锐,这是建筑师职业养成的习惯。感觉像是正在组合一个庞大图景,可是目前掌握的局部却非常有限。
我得知,林峰所在的机构近期参与角逐城南区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商业中心工程。
而这个项目的最大竞争对手,背后有很强的官方背景。
林峰,好像急着展示自己的能力,又急着得到一些……非经济方面的帮助。
这和我妻子的“演戏”有什么关系?
我想不通。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是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学弟,他如今在一家私家调查机构任职。毕业后彼此联系渐少,不过他仍然记得我的称呼。
陈阳学长,不好意思打扰。我这边……承接了一项比较特别的任务,或许与你有关。
我的心一沉。
“什么委托?”
“是查你妻子,徐薇。”
我握着电话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谁委托的?”
此事有禁忌,按规矩不能透露。不过,老师,我查阅过部分文献,觉得内情复杂。我认为,你理应了解真相。
他顿了顿,说:“徐薇老师的父亲,是不是叫徐建国?”
“是。”我的喉咙有些发干。
“他最近,是不是住院了?”
我愣住了。
岳父住院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徐薇从来没提过。
那位学长,我只能交代到这里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那边,心血管内科,具体是1302病房。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阳光很明媚,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岳父住院,这么大的事,她竟然瞒着我。
那个所谓的“家里的问题”,原来是指这个吗?
可这和林峰又有什么关系?
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最终汇成了一个必须去验证的行动。
我请了假,开车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找到了1302病房。
病房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
我透过那块玻璃情感挽回,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我的岳父,这位平时很强健,总在广场边对弈的老人,现在却无力地卧在病榻上,身上连接着许多医疗器械。
徐薇趴在床沿,目光向下,手持水果刀,正将苹果的皮细细地刮掉,动作缓慢而专注。
她的动作很慢,很专注。
苹果皮被削成完整的一长条,没有断。
我记得,她以前说过,这是她小时候,她爸爸教她的。
病房里很安静。
光线穿过玻璃进入室内,围绕着她形成一圈明亮的光环,然而她的身影显得十分瘦弱,孤零零的。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林峰走了进去。
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笑容。
他放下了那个装着水果的篮子,随即很随意地来到徐薇旁边,伸出手,覆盖在了她正在削苹果的手上。
“我来吧,你休息会儿。”
徐薇没有挣扎阳江哪里有小三侦探公司,她停下了动作,把刀和苹果都交给了他。
然后,她抬起头,对林峰露出了一个微笑。
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带着一丝讨好和依赖的微笑。
我站在门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先前所有的推测,所有的考究,在此刻,都化作了荒唐的笑柄。
原来,我才是那个局外人。
原先,在她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刻,站在她身旁的,不是自己,而是林峰。
我没有推门进去。
我甚至没有勇气再看下去。
我转身,一步一步地离开那条长长的走廊。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碎玻璃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天,黑得特别彻底,连一颗星星都没有。
我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
把学弟后来发给我的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翻来覆去地看。
报告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
徐薇的父亲叫徐建国,他以前在中学教书,已经退休了。不过,两年前,他开始沉迷于网上赌博。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后来,越陷越深。
他输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
而最大的债主,就是林峰父亲的公司旗下的一个小贷公司。
利滚利,那笔钱已经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催债的人找到了徐薇。
而林峰,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提出了那个“交易”。
他能协助解决这笔欠款问题,并且愿意承担徐建国今后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心脏不适的所有医疗开销。
条件是,徐薇要扮演他的未婚妻。
林峰的家族,属于世代经营商业的望族。他父亲总是催促他考虑婚事,他却不愿被婚姻所牵绊。他希望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以此平息家中反对的声音,同时需要一个持家有道的妻子,为他在城南那个项目的竞标增添家庭和睦的砝码。
徐薇,一个出身清白、气质出众的舞蹈老师,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报告的最后,附了几张照片。
徐薇独自一人,分别前往几台自动取款机,每次取出钱款,接着将钞票装入一个厚实的纸袋之中。
是她一个人,深夜在医院的走廊里,靠着墙壁,无声地掉眼泪。
她独自一人,面对林峰以及他商界中的那些伙伴,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容,一杯接着一杯地饮酒。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揉成了一团。
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事情。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那么疲惫,明白了她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这件事情是她父亲造成的麻烦,是她家的难堪。她不希望将这种污点和负担,牵扯到我们这个“无瑕”的居所。
她想保护我,用她自己的方式。
她想一个人,扛下所有。
因此她更愿意跟恶魔交换条件,也不肯向我这个丈夫,寻求帮助。
这份“保护”,对我来说,却是最残忍的背叛。
她没有把我当成可以同舟共济的伴侣。
她把我,当成了一个需要被保护的、易碎的、无关的局外人。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林峰,不是债务。
是她那份自以为是的坚强,和对我彻头彻尾的不信任。
这比任何背叛,都更让我感到寒冷。
我坐在黑暗里,直到窗外泛起了鱼肚白。
我做了一个决定。
徐薇是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
她看起来一夜没睡,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阴影。
她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愣了一下。
“你……没去上班?”
“我在等你。”我的声音很平静。
我没有把那份调查报告拿出来。
我只是看着她,说:“我昨天,去医院了。”
她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她手里的包,“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看到岳父了。”我继续说,“也看到林峰了。”
她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顺着墙壁,缓缓地滑坐在地上。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
压抑了很久的哭声,终于从她的喉咙里泄露出来。
那不是委屈的哭泣,也不是悲伤的哭泣。
那是一种,所有掩饰和戒备都完全瓦解时,绝望的、无助的呼号。
我没有过去扶她。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
等她哭声渐歇,我才开口,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
“为什么?”
她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
“对不起……陈阳……对不起……”
“我并非指这个。”我打断她,“我真正想问的,为何不将情况告知我?在你心目中,我究竟算是什么?是那种连岳父家遇到难题都无法分忧的懦夫吗?”
不是这样,她急忙摆动头部,不是这样,她只是,她仅仅是,不希望给你增添忧虑。
“不想让我烦心?”我重复着这句话,觉得无比讽刺。
你的项目极为关键,那凝聚了你一年的努力。我父亲……他干的事情,实在令人难堪。我如何能启齿?不希望这些不堪之事牵连你,更不愿让你看轻我们的家世……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
原来是这样。
过去在她观念里,我是个怎样的人呢,是个只顾钱财和琐事,从而轻视她以及她家人的家伙。
我们结为夫妻已经五年了,我以为已经为她打造了一个稳定富足的居所,一个能够让她倚靠的坚实臂膀。
到头来,在她心里,我却连最基本的信任和依靠都算不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这段婚姻的裂缝,不是从她遇见林峰开始的。
那是从很久以前开始的,在我们彼此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时,在我们各自埋头于事务,缺少沟通的日子里,它已经不知不觉地萌生了。
我埋头研读我的设计图,我的建筑构想,我以为我在为我们的前景添土加石。
我未曾察觉,这个家的根基,由于沟通不畅和彼此误解,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是我的错。
是我,把她推开了。
是我,凭借我自作多情的所谓“为你着想”,让她认为,她只能独自承受风霜雨雪。
这个认知,比知道她和林峰的交易,更让我感到痛苦。
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蹲下。
我没有碰她,只是看着她的眼睛。
“徐薇,你弄错了一件事。”
婚姻并非毫无缺点的理想构造,不允许存在任何小毛病。它更像是正在建设的地方,难免有脏乱,难免有嘈杂,难免会出现各种料想不到的状况。
“而夫妻,是工地上,唯一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工友。”
“你把我,当成了在工地外面,指手画脚的甲方。”
她愣愣地看着我,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这一次,我伸出手,轻轻地,帮她擦掉了眼泪。
“事情,我们一起解决。”我说。
我没有说“我原谅你”。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里,我们都有错。
这件事并非要求宽恕的议题,而是必须携手应对并加以调整的系统性挑战。
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又卖掉了我婚前购置的一套小公寓。
那套公寓,是我父母留给我,准备给我将来养老的。
凑够了钱,我给林峰打了电话,约他见面。
见面的地点,是我选的。
就在我设计的那个,即将竣工的图书馆的工地上。
林峰来了,还是那副精英派头。
我穿着一身沾了灰尘的工装,戴着安全帽。
我们站在图书馆巨大的落地窗前,下面是城市的车水马龙。
“钱,我还给你。连本带息。”我把一张银行卡推到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那张卡,笑了笑。
“陈阳,你以为,我缺这点钱吗?”
我清楚你并不匮乏,我望着他,徐薇,她是我配偶,她的责任,便是我应承担的义务,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亏欠。
你确实比我预料的,更有责任感。林峰的目光中,显露出几分探究。
“这不是担当,这是本分。”
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讲道:我明白你这样做的缘由,城南那个工程,以及你家里的难处。你借助了徐薇的窘境,将她当作你的手段。如今,这个手段,我要拿回来了。
林峰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凭什么?”
仅因为我与她结为夫妻。我直视他的眼神,清晰表达观点。金钱或许能解决部分麻烦,但情感纠葛非此可化解。你无法触及她的内心,因为她情感归属并非在你这边。
我指了指脚下的建筑。
观察这座建筑,它得以落成,凭借的是钢筋,是混凝土,是每一个扎实的构造。并非依靠那些徒有其表、仅作形式审查的附加物。
“你和徐薇的关系,就是那些装饰。而我跟她,是里面的钢筋。”
可能此刻,部分梁柱已锈蚀,某些构造已损坏。不过只要主体稳固,我定能将其修补完整。
林峰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窗外,又看了看我。
最后,他拿起了那张银行卡。
这笔钱我接受,算是,我为我父亲,因他那些不光实的交易,说声抱歉。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陈阳,你是个不错的对手。徐薇,她比我想象的,要幸运。”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解决了债务问题,我们生活里最大的那块石头,被搬开了。
但搬开石头后,露出的,是下面被压得坑坑洼洼的地面。
我和徐薇之间,并没有因此就立刻回到从前。
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信任,如同明镜一般,一旦出现破损,即便加以修补,仍旧会显现出那道难看的痕迹。
我们开始尝试着交流。
我跟她讲我工作上的压力,她也跟我说她父亲后续的治疗。
我们不再分房睡,但躺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像是隔着一条河。
我能感觉到她的努力。
她会像以前一样,给我煲汤,等我回家。
她会主动问起我图书馆项目的事。
但我知道,我们都回不去了。
那段“演戏”的日子,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们两个人的心里。
我一闭上眼,就能看到她和林峰站在一起的样子。
她一看到我沉默,眼神就会变得不安和愧疚。
我们的家,已不再是寂静的背景,而是转变成一个谨慎的修补场所。
我们都在努力,但我们都不知道,这栋建筑,还能不能修复如初。
我开始觉得疲惫。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种小心翼翼的关系的疲惫。
我需要空间。
一个可以让我自己静一静,想清楚我们未来的空间。
我订了一张去南方的机票。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当时参与了一项古建筑修缮工作情感挽回,我一直都想去那里参观。
我告诉徐薇的时候,她正在浇花。
水壶里的水洒了出来,打湿了地板。
她没有去擦,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你要走?”
“嗯,去一段时间。”我说,“我需要……换个环境。”
“是……因为我吗?”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沉默了一下,说:“是我们。”
“是我们都需要空间,想一想,以后要怎么办。”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地上的水擦干。
那几天,她开始帮我收拾行李。
我的每一件衣服,她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叠好放进行李箱。
她的话变得很少,但眼神,却总是在我身上。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件即将失去的珍宝。
去机场那天,是她开的车。
一路无话。
车里的电台,放着一首老歌。
“当爱已成往事。”
我伸手,关掉了电台。
车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清浅的呼吸声。
到了机场,她帮我把行李箱拿下来。
“我送你到安检口。”她说。
我们并肩走在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
周围很嘈杂,但我却觉得,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走到登机口,提示登机的广播响了。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她。
“我走了。”
“嗯。”她点点头,眼圈红了。
“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爸。”
“嗯。”
我伸出手,想抱一下她。
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我还是做不到。
我转身,准备走向登机口。
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刻,她突然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臂。
她的手很用力,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
“陈阳,别走。”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惊惶和无助。
请不要离开,好吗?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确实知道错了。我们可以重新来过,我们肯定能够成功的。
周围的人,都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她像是完全没有察觉。
她只是死死地抓着我,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求你了,陈天,别丢下我一个人。”
她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打湿了我的衣袖。
我望着她,望着这位与我相伴多年的伴侣,此刻她在我眼前,宛如稚童般失态。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但我知道,我不能心软。
心肠太好,容易让我们再次陷入那个谨慎的、麻烦不断的过去状态中。
我缓缓吸气,另只手,轻柔中带着决断,一根根,将她手指分开。
她的手,冰凉。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充满了绝望。
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徐薇,”我说,“不要再碰我。”
我看到她瞳孔猛地一缩,脸上所有的血色都褪尽了。
她像是没站稳,身体晃了一下。
我没有去扶她。
我只是继续看着她,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说完了我的话。
“这不是在惩罚你,也不是在拒绝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都病了。我们的婚姻,也病了。”
此刻,我们应当做的,不是装作风平浪静,不是死死地缠住彼此不放,而是要彼此让步一些,给自己,也给对方,一个疗愈和放松的余地。
我们应当首先掌握,独自一人如何稳健地站立。接着,才可以商讨,是否需要再度相聚。
“那边,”我示意了彼此,那一点空间,“便是我们疗愈的开端。”
说完,我没有再看她。
我转过身,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了登机口。
我没有回头。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像钉子一样,一直钉在我的背上。
直到我走过拐角,那道目光,才终于消失。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
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第一次,让我有了一种疏离感。
我的前景,我和徐薇的前景,都似天边浮絮般,变幻无常。
但我心里,却 strangely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知道,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